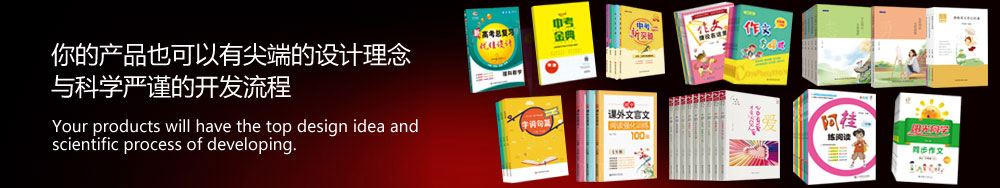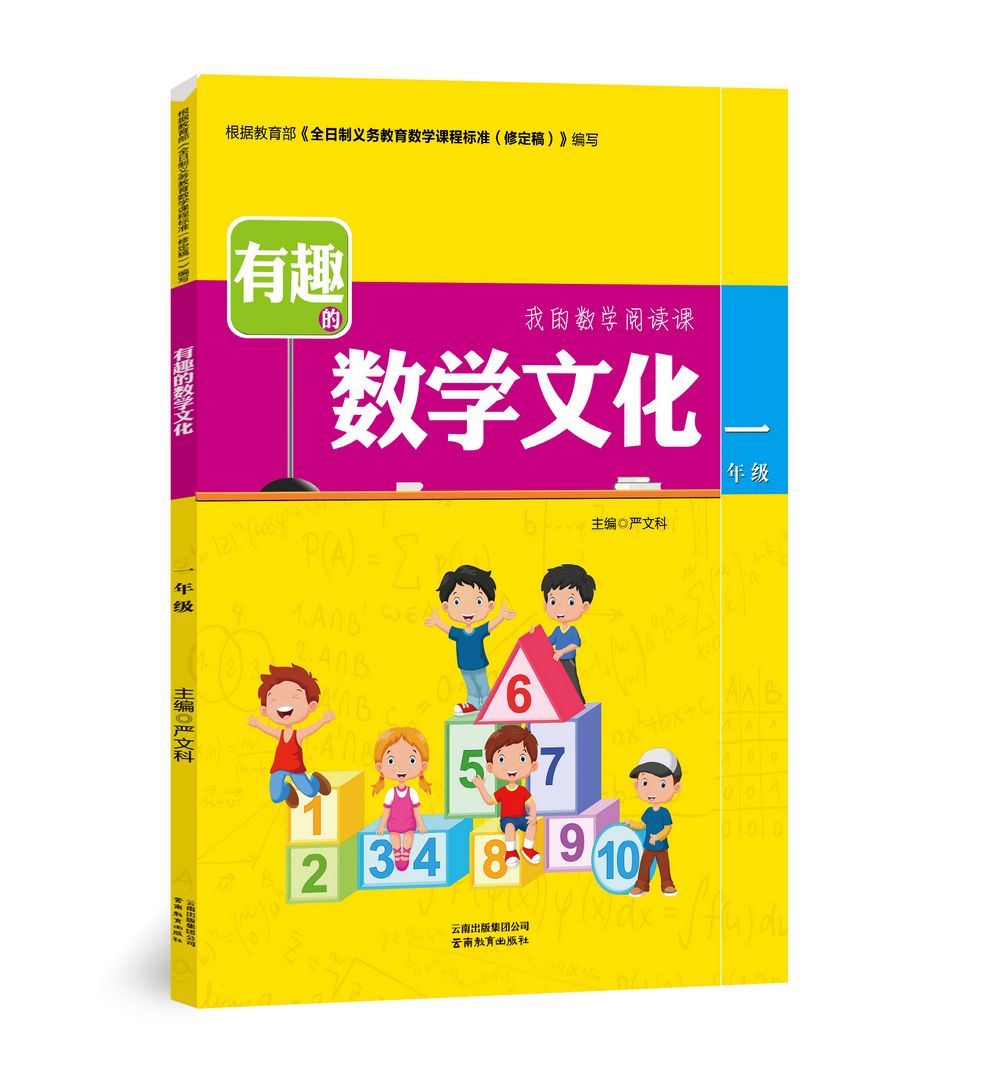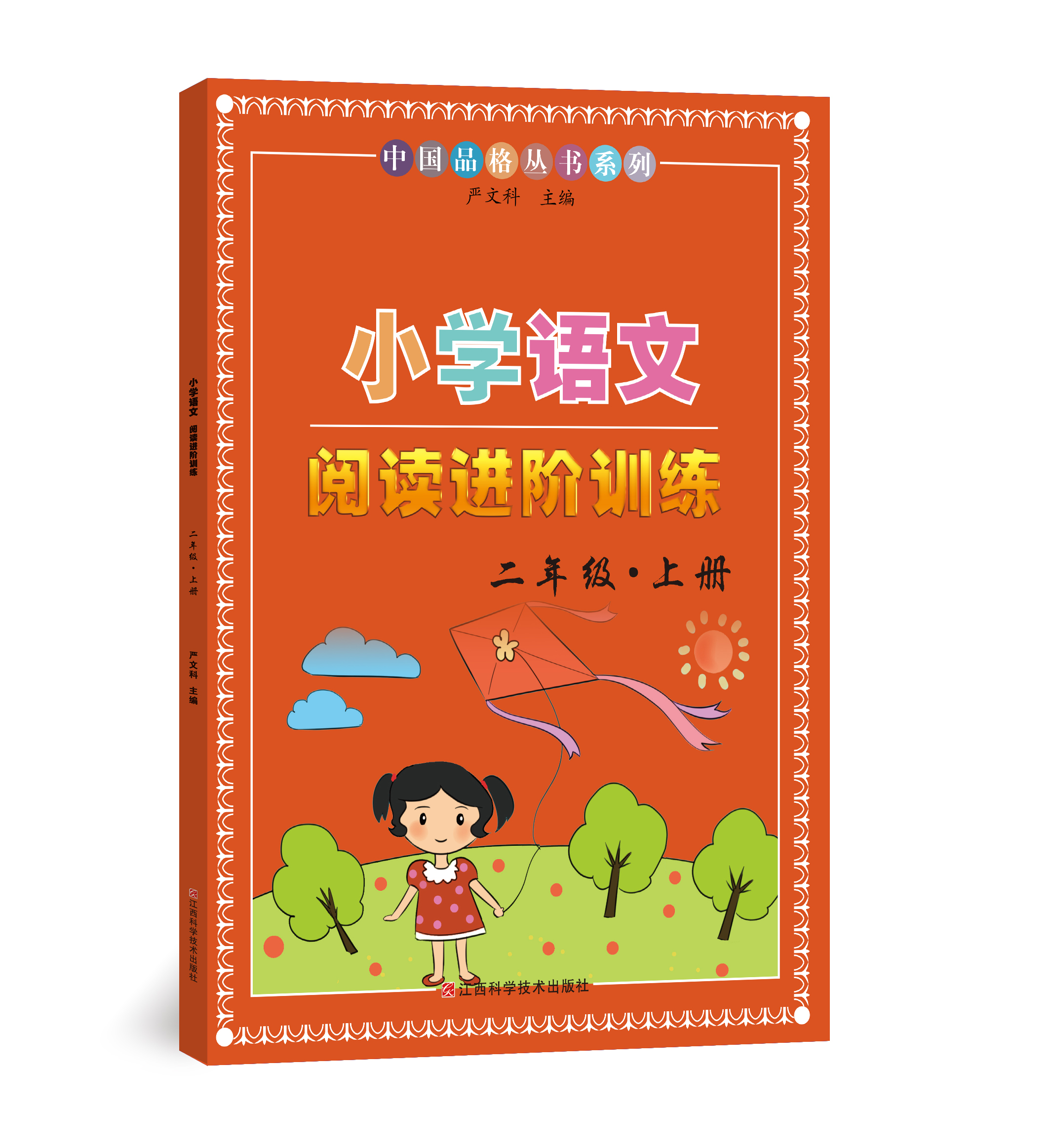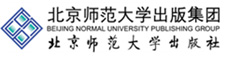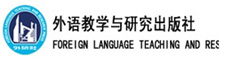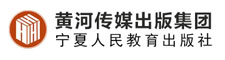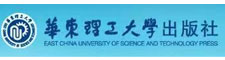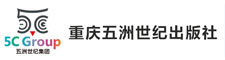在新改革征程中构建出版协同开放新格局
站在中国“新改革元 年”的原点上,时代的涌流扑面而来。天地经纶,风雷激荡,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徐徐展开。回首2013,国际局势乱云飞渡,而中国大地沉着磐如。 新作风、新思维、新提法、新调整,凡此种种带来的新气象、新格局、新震撼,都指向为民务实清廉之风的新回归。沉潜爬梳,应势而动,为2014乃至未来十年 的再爆发、再成长,积蓄了再腾跃的新能量。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新近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正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政治经 济的大气局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主旋律、主色调,自然也为出版产业的繁荣发展确立了主题词。
在“全时代”、“云时代”、“微时代”,对文化产业需要再认识,必须将之纳入国家“五位一体”的大棋局之中,从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坐标系中,笃守文化又跳出文化,沉潜出版又跳出出版。
全球化造就了全方位、全视阈、全媒体的“全时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国内因素、国有民营力量实现了大融通、大集结、大盘整,文化与经济一样快速进入 了国际大循环。云计算、云数据、云服务造就了“云时代”,虚拟与现实、线上与线下,实现了零距离、零差别、零库存,上演着“双十一”、“双十二”等等的网 络经济神话。而微博、微信、微电影等等造就了“微时代”,粉丝经济伴随各种新媒体蓬勃生长,创造了媒介经营的无限空间,激发了文化消费的无限遐想。
毫无疑问,文化的地位在上升,文化的边界在模糊;文化的实力在增强,文化的属性在变异;文化的传播在扩大,文化的影响在分化。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迫使 我们必须从内部洞悉文化的规律回归文化的本质;必须从外部辨析文化的边界调适文化的功用,既不固步自封孤守清高,又不随意泛化随波逐流;必须在新的时代发 现文化的新规律,迸发创意的新活力。
党 的十八大确立了未来10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方略,凸显了文化强国战略下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性。十八届三 中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文化体制改革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工作导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 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这从党和国家意志上,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勾画了宏阔 的蓝图。文化再不能安逸于传统的宣传性文化领域内,孤立地谋划改革,封闭地谋求发展。文化产业注定要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势一起,经历“换档期”、承受 “阵痛期”、迈过“消化期”;注定要重新理解、深入把握文化产业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注定要在转方式调结构、保民生促开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转型中,把握契机、寻求商机、化解危机。
长期以来,文化、精神生产领域一些业者习惯于偏安一隅,自得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隔膜于政治、陌生于经济、远离于社会,以恪守“清流”来规避政治、回 避责任、逃避民生,反映到现行的出版改革领域,内容创作、编辑策划、市场营销的封闭性、条块性、孤岛性、壁垒性依然顽固地束缚着出版发行业的活力。文化产 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行业,就必须让文化融入国家的大战略,进入“五位一体”的大布局。
文化的核心是内容创意,文化的本质是精神濡染,文化的要义是振民育德,文化的路径是公共服务。笃守文化,就是要忠于文化理想,执着文化价值,张扬文化创 新;而跳出文化,就是要将文化置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大背景下,重塑文化的形象,重绘文化的版图,致力于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金融联姻,文化与生 态和谐。同理,深潜出版,就是要坚守“为人作嫁”品德,精益求精,唯品质是求;而跳出出版,则是要看到出版的业态、载体、传播、消费等形势的新变,从策划 组稿向经营作者整合资源转变,从书稿编辑向开发版权产业转变,从图书发行销售向出版多业态大平台建设转变,唯其如此,方能因势而变,应势而作,顺势而为。
在已然开启的中国新改革浪潮中,要赢得出版产业改革发展下一个“黄金十年”,需要准确把握出版改革的规律,深刻理解出版文化的价值,精准洞察出版产品的消费,立足内容又跳出内容,做强主业又跳出主业。
对于出版体制改革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历经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自2003年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洗礼,已经到了可以总结需要总结、可以反思需要反 思、可以明晰需要明晰的阶段。比如,创作的个体性与产品的大众性、出版的精神性与产业的规模性、思想的导向性与商业的价值性、文化的精英性与服务的公共 性,等等,需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明确,形成文化事业出版产业的理念自觉、道德自觉和商业自觉。更加注重出版作为内容创意的内在性、内生性和内蕴性,更加注重 出版内容创新与组织流程的主体性、主导性和主流性,更加注重出版产业作为精神产品消费的精神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应当摆在一切改革的首位。文化越是泛化, 价值越要坚实;业态越是多元,内容越要纯净。改革的目的,是壮大内容生产,提升内容品质,扩大内容消费;改革的路径是激发主体动力,迸发创造活力,增强竞 争实力。做强做大的指向,应该是内容创造、精神产品创新,而不是或不仅仅是GDP。做大做强的路径,可以是产业化、IPO,但显然不能唯产业化、唯 IPO。在精神生产领域,有没有GDP崇拜现象,有没有产能过剩,有没有价值失矩、生态失衡?值得我们警醒深思。如何让市场在内容创意产业领域的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显然还有许多规律需要发现摸索。
文化消费提上了国家战略,出版业能不能抓住商机,取决于我们对出版价值的重识。当价值与消费之间发生梗阻时,我们发现,其实业界对出版价值的理解或偏 颇或错位,或势利或单纯,或超验或落后。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存在两极分化:片面理解历史传承价值,以简单的“复古”代替文化的积淀; 片面理解市场价值,以单品的畅销掩盖产品主线的“缺钙”,而出版的当代性、建设性、服务性和实用性却难以真正体现。
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对出版价值认识的失衡,影响着对读者消费需求的真切了解,对渠 道建设的切实贯通、对全媒体时代营销手段的充分运用。相当部分业者更主要关切的是实现销售回款,而忽视实现图书的精神共鸣或者图书的生产力转化。实体书店 危机也好,互联网数据定位优势也罢,并未普遍地强化业界对市场需求调研的意识,对读者阅读信息分析的渴求、对客户关系数据的有效挖掘。于今,年出书品种不 断猛涨,而单品效益大幅下滑;新书生产不断扩容,而细分市场不断稀释,印数持续降低,库存持续上升。我们绝不能以读者分流、阅读个性化来掩盖我们粗放经 营、价值与消费错位的痼疾。一些全心全意为“三农”为基层为民众服务的“真经”,不少业者却未能深入习鉴,不能不令人唏嘘。
当今文化泛化持续扩大,内容的边界日益弥漫,出版的业态快速变异,正唯其如此,才需要我们愈加清醒、愈加坚定、愈加“保真”。违背出版文化的规律,注定要多走弯路、饱尝苦果。
立足内容,当然要做实内容、做精内容、做新内容、做久内容;跳出内容,是要关心内容的积聚、内容的传播、内容的转化、内容的再生。只有关心内容的去向、 内容的实现、内容的口碑,才能立足好内容。做强主业,要有坚实的内容作基础,这不难理解。难以化解的是,主业漂移、主业泛化正越来越成为做强做大的“主流 逻辑”;难以掌控的是,为了做强主业,不得不去做强副业;难以评价的是,做大主业,部分做强出版,其内容影响力之光鲜可能掩盖了其市场份额占比。不论仁者 智者,面对竞争面向未来,都不得不跳出主业来看待主业。跳出主业,或许更能看清主业的优势、主业的价值、主业的稀缺。必须明了,不论什么时代、何种情形, 主业就是主业,内容就是内容,市场就是市场。
在“后集团化”时代、“后转企改制”时代,出版要继续作为主力军,守住主阵地,当好排头兵,就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深处着力,精准发力;就必须走创新之路、融合之路、开放之路,激活主体又锁定主体,搞活市场又管住市场。
出版体制改革在经历了第一个“黄金十年”之后,进入了“后集团化”时代、“后转企改制”时代。随着行政捏合的阵痛逐渐退去,员工身份转换完成社保体系 初建,集约化企业化带来了资产的物理规模效应,国家项目资金扶持政府采购大增弥补了一定的市场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有一种情绪、一种惰性或已悄然浮现,即 下一步的改革似乎无甚作为,动力不足、目标不清。或以企业行政管理代替法人治理,或以股改上市代替体制改革,或以市场营销代替机制创新,或以文化回归代替 产业发展。凡此种种,均高度警示出版发展无止境,改革无止境。就宏观方面,按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需要在管理体制、生产机制、市场体系、公共服 务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就微观层面,需要在企业组织、主体活力、运行机制等方面持续强化改革。中央提出,要以问题为导向,深处着力,精准发力。对于出版体 制改革第二个十年,战略目标当然不能游离于转方式调结构,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大方向。而突出的问题就是主体 的活力、创新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不足、不强。要破解“四力”疲弱,出路在于三大向度:创新、融合与开放。
时下,创新已然成为出版产业的口头禅,令人尴尬的是,创新并没有大面积地播种,带来大面积的高产稳产田。观念上,创新更多地被转嫁给作者,而不少出版 者茫然于依附、游离的地位;现实中,利润的考核、市场的催迫,更使得创新被层层盘剥,重复出版、平庸出版、跟风出版,更是极大地挤压和挫伤创新的空间。
从何创新?大要有五:一是观念创新。必须破解编辑在内容创新中的从属地位、被动地位,同时,也要破除出版创新的自我藩篱,从单一作者单本图书向资源集 聚、产业价值链拓展转变。二是内容创新,需要运用激励机制、评价机制、资源开发机制与版权保护机制等,使作者原创与编辑策划与终端消费三方乃至多方有效高 效互动互促。三是制度创新,通过组织管理、运作、规制的创新,形成组织运营的高效化、机制化、自组织化,以此激发和激励出版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技 术创新,这是出版业当前最大的短板之一,也是作者以及编辑们的能力危机之一。当今互联网新媒体移动通讯等技术力量正迅速改变了内容创作的旧规则、旧面貌, 甚至成为内容的组成部分,绽放出创意的绚丽色彩。离开新技术滋养的出版创新之花,终将苍白而颓败。五是发展创新。毋庸讳言,这是中国出版产业的薄弱环节, 客观去看,长期以来出版业发展方式严重老化、商业模式创新严重落后的情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以致于业界难以根本摆脱线性的编辑加工、印发销售的单向模式, 难以根本跳脱靠品种数量、码洋定价求增长的粗放模式,发展方式的创新已经迫在眉睫。产业链的创新、资源整合的创新、版权产业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新媒 体应用的创新等等,与控制产能、优化结构一样已经刻不容缓。
融合是时代主旋律。文化与经济融合,出版与科技融合,国有与民营融合,国内与国际融合,制作与终端融合,编者与著者及至读者融合,已经成为鲜活的现实。 如果说,两年前当本报首提阅读产业、传媒产业与创意产业三大路向之时,业界尚有不解或淡漠,那么,今天,三大产业融合发展已然燎原成蓬勃之势。出版正可在 其间长袖广舒、纵横驰骋。融合,当然不是以牺牲主体为代价,以消弭主导权为条件。融合,需要找准接口,掌握端口,守住出口;需要洞识几务,同声相应,共创 共赢;还需要谨防排异现象、水土不服、盲目嫁接。
开放是国家大势,也是文化的天然要义。文化要化成天下,必然要求通达四海,不分贵贱高下、地域民族。然而,长期以来,利益的壁垒、体制的束缚、标准的障 碍、物流的局限等等,横亘在出版发行改革发展之中。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几十年历尽波折步履艰难。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郑重入列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议,标志着出版市场体系建设纳入了文化市场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之中,进入了全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堪称是重大的转折点,关键的里程碑。
建设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是十八大确立的新战略,对出版文化产业改革繁荣发展也有着重要指向意义。开放意味着进一步开放准入、开放资源、开放主体、开放市 场、开放竞争,意味着开创资源配置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竞争的公平规则,意味着市场主导下垄断、霸王等一切不利于出版文化生产要素自然流动、精神产品自主供需 的陈规旧习或新规新派,都要接受开放型经济的检验。文化要融入开放型经济的大潮之中,出版不可能独善其身、独享其成。出版业界要善养开放的胸襟、做好开放 的准备、构造开放的格局、成为开放的中坚。
改革首要的是解决动力问题,即关涉主体。在当今经济、技术、社会风云急遽变幻的时代,文化出版的主体也迅速发生质与量、内与外的异变。体制的改革、三 跨的发展、股权的探索等等,使出版主体或分解或转移或叠加或增生,而数媒新媒、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催生了一大批自媒体人、自助出版人、自文化营销人。主 体多元不是坏事,可以激发活力、刺激竞争,焕发创造动能。但主体混杂的状况,又需要我们厘清主体身份、锁定核心主体、打造主流主体,需要巩固传统主体、培 育新兴主体、引导从众主体、抑制变质主体。主体不清、主体放任,必将贻害无穷。
改革终极是要解决出路问题,即关涉市场。市场表象上是供需关系,实质上是制度关系。制度经济学表明,组织与交易成本在市场经济中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而 经济制度的进化影响甚至决定了市场的“钱景”。新制度经济学催生了产权经济学,对于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有着强烈的借鉴意义。搞活市场,就是要搞活生产要 素配置的制度,搞活劳动人事分配的制度,搞活知识产权权益与置换的制度等。而所谓管住市场,就是管住市场准入、市场交易的制度,管住市场导向、市场产权的 制度。打破垄断、突破地域、畅通供需,不过是系统性制度变革的题中之义,不是中心,更不是全部。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季,中国出版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二个“黄金十年”。仿佛一切都在蓄势待发,这是春雷炸响的前夜,这是春芽破土的先声。固本筑基,与 时偕行,谋先但不要抢跑,谋远但不要超验,放开眼界,做大格局,突破自我,重绘版图,将是中国出版产业繁荣发展的天则之选。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在2013年阔步迈向了“更新纪”,实现了58年来的第三次、18年来的第二次华丽转身。秉持惟优惟新、利业利世的核心理念,开启了阅 读产业、传媒产业和创意产业融合协进的新征程新使命。创新、融合、开放,规律、价值、消费,出版、内容、主体,这些关键词、主题词,将始终作为新商报在兹 念兹,服务于出版产业、传媒产业、创意产业的微言大义,新商报将坚定不移、忠实信守,与业界同仁一道,为实现文化强国、出版强国梦而共襄盛世,同心同德、 共创共赢。
文章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